
民国十七年的上海,黄浦江的水泛着煤烟色的光,外滩的钟楼刚敲过十二点,法租界的街道却已亮起昏黄的灯。黄金荣坐在公馆二楼的红木椅上,指尖摩挲着翡翠烟嘴,目光扫过跪在面前的少年——阿强。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竹布衫,膝盖沾着泥,却挺直腰板,眼神里带着股子倔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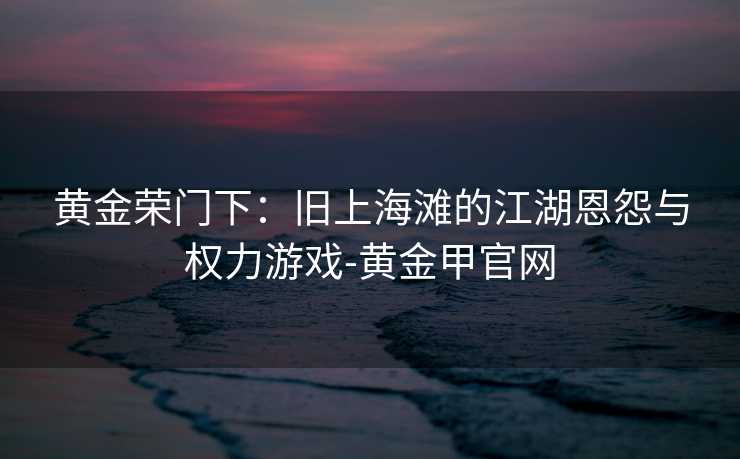
“你叫什么?”黄金荣吐出一口烟,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“陈阿强,码头扛包的。”少年的喉咙发紧,却没低头。
“为何要拜我为师?”黄金荣眯起眼,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。
“前天夜里,您在十六铺遇刺,是我扑过去挡了一刀。”阿强抬起胳膊,袖口露出半截伤疤,“我欠您一条命,想跟您学本事,混出个人样。”
黄金荣没说话,只是盯着那道疤看了许久。忽然笑了:“好,从今天起,你就是我的干儿子。”说罢,他拿起桌上的玉佩,塞进阿强手里,“这物件能保你平安,往后跟着我,别丢了性命。”
阿强成了黄金荣的干儿子后,日子像坐上了黄包车——快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每天清晨,他要跟着师傅去茶楼听消息,看报纸上的黑道新闻;中午要在公馆里伺候客人,倒茶递烟;晚上则跟着兄弟们去巡场子,处理地盘上的纠纷。最让他头疼的是那些“师叔”,比如杜月笙的徒弟万墨林,总爱找茬:“你算什么东西?也配跟在荣爷身边?”每当这时,阿强只能咬着牙忍,直到黄金荣出现,冷冷地说一句:“阿强是我的人,谁敢动他?”那些人才会讪讪退去。
可江湖哪有永远的平静?民国十八年春天,法租界来了个新巡捕头,叫史密斯,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国佬。他看不惯青帮的走私生意,接连查封了几家赌场和烟馆。黄金荣震怒,拍着桌子骂:“这洋鬼子是想断我们的财路!”当晚,他就召集手下商议对策。阿强站在角落里,听着他们讨论如何对付史密斯,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要是能除掉这个巡捕头,师傅肯定会重用自己。
机会来得很快。几天后,史密斯要去参加一场慈善晚宴,路线早已被青帮摸清。阿强主动请缨:“我去杀了他,保证手到擒来。”黄金荣犹豫了一下,还是点头答应了。那天夜里,阿强埋伏在宴会厅外的巷子里,握着匕首的手全是汗。当他看到史密斯走出来时,正要冲上去,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低喝:“住手!”回头一看,竟是杜月笙。
“你想干什么?”杜月笙皱着眉,“荣爷说过,不准乱杀人。”
“这是师傅的命令!”阿强急了,“我要为师傅分忧!”
“分忧?”杜月笙冷笑,“你要是杀了史密斯,洋人会派军队来围剿我们,到时候整个上海滩都要遭殃!你以为这是英雄?这是蠢!”
阿强愣住了,手里的匕首慢慢垂下来。杜月笙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跟我走,我带你去见荣爷。”
回到公馆,黄金荣正在抽鸦片,看见阿强和杜月笙进来,放下烟枪问:“事情办妥了?”
“没有,”阿强低下头,“我想杀史密斯,被杜先生拦下了。”
黄金荣沉默了一会儿,忽然笑了:“做得对。江湖不是靠杀人混出来的,是要讲规矩、讲情义的。”他转向杜月笙,“月笙,你这孩子教得好。”
那一刻,阿强终于明白,原来江湖不是只有打打杀杀,还有人情世故,还有权衡利弊。他看着杜月笙,心里涌起一股敬佩——这个师叔,比他想象中更有头脑。
然而,好景不长。民国二十年,日本兵打进上海,黄金荣的势力逐渐衰落。阿强跟着师傅去了香港,可没过多久,黄金荣就病倒了。临终前,他把阿强叫到床边,递给他一张纸条:“这是我留给你的东西,以后好好过日子。”
阿强接过纸条,上面写着几个地址和一笔钱。他哭着问:“师傅,您还有什么话要说?”
黄金荣笑了笑,声音微弱:“江湖啊,就像这黄浦江的水,看似浑浊,却藏着许多秘密。你要记住,不管做什么,都不能忘了良心。”
说完,他便闭上了眼睛。
黄金荣死后,阿强拿着那张纸条,回到了上海。他没再涉足江湖,而是开了一家小饭馆,取名“荣记”。每天清晨,他会站在门口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想起当年跪在师傅面前的那一夜。他知道,自己 never 真正离开过那个江湖,因为师傅的话,已经刻进了骨子里。
如今,上海的老街坊们还会说起“荣记饭馆”,说起那个曾经是黄金荣干儿子的老板。有人说他傻,放着大好的江湖路不走,偏要守着个小饭馆;也有人说他聪明,懂得急流勇退。而阿强自己知道,他想要的,不过是平凡的日子,和对得起良心的生活。
毕竟,江湖再大,终究抵不过一颗安稳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