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整理祖母遗物时,我在樟木箱底层摸到一张薄如蝉翼的黑白照。指尖触到照片边缘的毛边,像是碰到了岁月磨旧的丝绸——那是祖父年轻时工作的珠宝店,而核心位置,正是那座闪着冷光的黄金柜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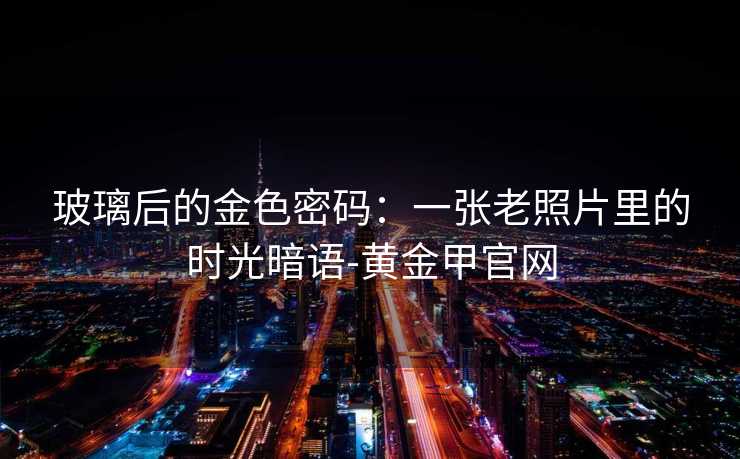
照片里的黄金柜台像一块凝固的月光,玻璃表面映着模糊的天花板吊灯,柜台上码放着金手镯、金项链,还有一枚嵌着红宝石的胸针,在黑白影调里仍透着灼目的亮。祖父穿着藏青色制服站在柜台后,领口别着银质工牌,嘴角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,仿佛下一秒就要为顾客递上托盘。我忽然想起祖母说过的话:“你爷爷那时最骄傲的不是卖了多少金子,而是看着客人戴上首饰时眼睛发亮的样子。”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城,黄金柜台是百货公司的“镇店之宝”。那时的黄金不像现在这般泛滥,更像一种庄重的仪式——姑娘们攒半年工资只为买一条金项链做嫁妆,老太太们把压箱底的银元换成金戒指,连小孩过满月,长辈也会塞个金锁片。祖父常说,他经手的每一件黄金饰品都藏着故事:对面裁缝铺的王婶为了给儿子凑学费,卖了陪嫁的金镯子;巷口修鞋匠的老伴,临终前把珍藏多年的金耳环送给了照顾她的护士。那些金闪闪的东西,不只是金属,更是普通人生活里的光。
如今再去商场,黄金柜台早已换了模样。玻璃幕墙反射着LED灯的冷光,导购小姐穿着职业套装,手持平板电脑讲解“克减”“以旧换新”的优惠。曾经手工雕刻的花纹被机器压制的几何图案取代,柜台里的黄金饰品琳琅满目,却少了些温度。我拿着手机对着祖父的照片拍摄,屏幕里的黄金柜台突然变得清晰——原来祖母一直把它放在相框里,摆在客厅的茶几上,每次擦桌子都要仔细拂去上面的灰尘。
那天晚上,我翻出祖母的首饰盒,里面躺着一条细金的项链,坠子是个小小的福字。记得小时候我问祖母为什么总戴它,她笑着说:“这是你爷爷当年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,他说以后我们的日子会像金子一样亮堂。”我把项链贴在脸颊,冰凉的金属传来微弱的暖意,忽然懂了照片里祖父眼底的温柔——那些被黄金承载的记忆,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。
后来我把照片扫描进电脑,调成复古色调,做成手机壁纸。每当看到玻璃后的金色轮廓,就会想起祖父站在柜台后的样子,想起那些关于勇气、爱与希望的故事。黄金或许会贬值,但藏在其中的时光暗语,永远闪烁着人性的光芒。就像祖母说的:“真正的宝贝从不在价格标签上,而在它陪你走过的每一个日子。”
如今,那张老照片依然躺在我的书桌抽屉里,偶尔拿出来看看,玻璃后的黄金依旧明亮,而我终于读懂了祖父未说出口的话:有些东西,永远不会过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