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晨光刚爬上窗台,楼下早餐铺的香气便裹挟着热气钻进楼道。我攥着豆浆杯站在路口,目光却被那堆码成小山的金黄饼子勾住——焦褐的边缘泛着油光,像撒了层碎金,空气中浮动着玉米特有的甜香,混着芝麻与葱花的气息,瞬间将我拽回了二十年前老家的灶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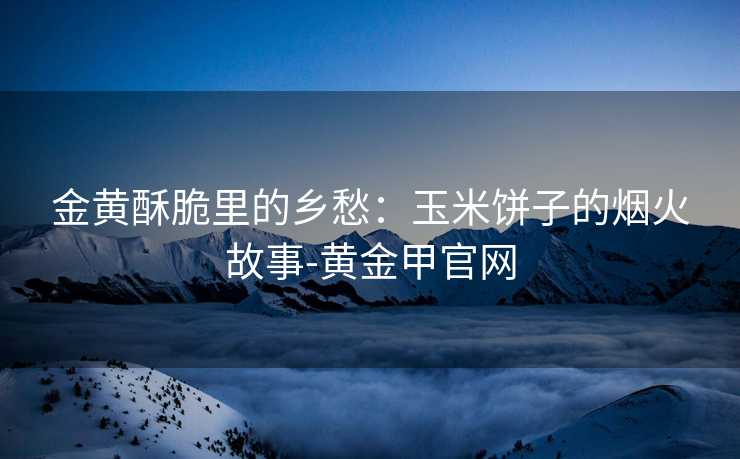
那时我还扎着羊角辫,每天天不亮就被妈妈拍醒:“快起,今早烙新玉米面!”灶膛里的柴火烧得噼啪响,铁锅烧热后刷一层薄油,妈妈抓起一把玉米面在掌心搓圆,轻轻按扁,丢进锅里。面团接触热锅的瞬间,“滋啦”一声,边缘迅速鼓起小泡,像绽放的小花。她用铲子快速翻面,另一只手捏着面剂子续上,动作娴熟得像在跳一支古老的舞。
“小心烫!”妈妈总在我凑近时把我往后推,可我还是会偷偷伸手,指尖碰到刚出锅的饼子,烫得直甩手,却忍不住往嘴里塞。外皮焦脆得掉渣,内里软乎乎的,混着葱花和芝麻的香,连呼吸都染上了甜丝丝的味道。那时的我哪里懂,这看似简单的饼子,背后是奶奶传给妈妈的秘诀:玉米要选秋天的“金皇后”,晒足三天才碾成面;和面得用井水,水温不能高也不能低;烙饼时要不停转动锅铲,让每一面都均匀受热……这些细节,像刻在基因里的密码,随着岁月沉淀,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,早餐店里的煎饼果子、包子馒头琳琅满目,我却总找不到那种熟悉的味道。直到去年春节回家,妈妈又端出一盘玉米饼子,我咬了一口,还是记忆里的香。“现在卖玉米面的少了,”妈妈擦着手说,“都是机器磨的,没以前那么香。”我突然鼻酸——原来最珍贵的味道,从来不是标准化生产出来的,而是有人愿意花时间,把对家人的爱揉进每一寸面里。
如今我也试着学做玉米饼子,却总掌握不好火候。要么烙得太硬,要么内部夹生,可即便如此,当第一缕香气飘出来时,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蹲在灶边等饼子的女孩,想起妈妈额头的汗珠,想起奶奶坐在藤椅上教妈妈和面的样子。原来食物的意义,从来不止于果腹,它是时间的容器,装着亲情、记忆,还有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烟火温情。
走在上班的路上,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早餐铺的玉米饼子。它们依旧金黄,依旧诱人,而我终于明白,所谓乡愁,不过是一张张金黄的饼子,一口口暖心的滋味,在岁月的长河里,永远鲜活着我们对家的眷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