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深夜的工坊里,煤油灯摇曳着暖黄的光晕,落在一块巴掌大的黄金胚子上。老匠人李德昌握着细砂纸,顺着兔头的轮廓慢慢摩挲——这是他做了三十年的活计,可每次碰到这只“玉兔”,手指还是会不自觉地发颤。兔耳尖微微翘起,像刚听见草丛里的动静;眼眶里嵌着的两颗黑玛瑙,泛着幽深的光,仿佛藏着千年前的月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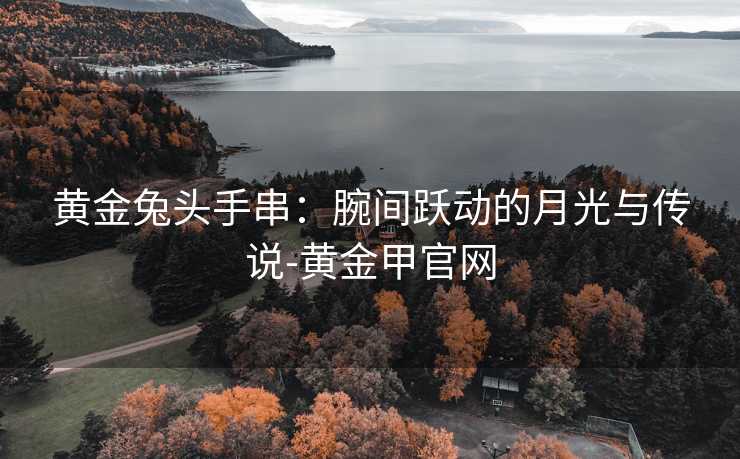
这枚兔头手串的诞生,要从去年冬天说起。那时镇上的古玩店老板捧来一尊唐代银兔俑,说想请李德昌复刻成首饰。“你看这耳朵,”老板指着俑身上的纹路,“唐代的工匠多讲究,连兔毛都刻得根根分明。”李德昌盯着那尊银兔,忽然想起自己过世的妻子——她生前总说,要是能把天上的玉兔戴在腕上,该多好。
于是他翻遍古籍,又在后山守了三天三夜,观察野兔奔跑时的姿态。终于,在一个满月之夜,他在熔炉前敲下了第一锤。黄金的液态流沙顺着模具缓缓淌下,冷却时发出细微的“叮”声,像玉兔踩碎了一地月光。
如今,这串手串躺在玻璃柜里,链子是细如发丝的金丝,每一节都缠着云纹,像给玉兔系了条飘带。常有年轻姑娘凑过来问:“这兔子怎么眼睛这么亮?”李德昌总是笑着答:“那是把月亮藏进去了。”其实他知道,真正的秘密在链扣处——那里刻着一行小字:“愿君如月,岁岁常明。”这是妻子当年的笔迹,是他偷偷錾上去的。
上周,有个穿汉服的女孩抱着相机跑进来,非要拍这串手串。她说自己的外婆临终前念叨着“玉兔”,却没来得及戴上什么信物。“您能给我讲讲吗?”女孩的眼睛亮晶晶的,像极了当年妻子的模样。李德昌把她带到工坊后面的小院,指着一棵老桂树说:“你听,风里有桂花香呢。”女孩愣了一下,随即笑起来:“我外婆也爱种桂树,说中秋时要摘桂花做糕。”那天下午,阳光穿过树叶洒在黄金兔头上,女孩举着相机拍了很久,末了还鞠了个躬:“谢谢您,让我看见了我外婆的月亮。”
如今,那串手串已经跟着女孩去了远方,可李德昌的工坊里,又摆上了新的黄金胚子。他时常会摸出块旧布,擦了又擦那个空了的玻璃柜——那里曾住过一只会发光的玉兔,住过一段未说出口的思念,也住了整个工坊的月光。
偶尔有顾客问起:“老师傅,您做的兔子,为啥总带着股仙气?”李德昌会抬起头,望着天上的月亮笑:“因为啊,每只玉兔都记得,自己是奔着月光来的。”
(全文约750字)